《庆余年2》第15集中,御史赖名成下线,又一段特不有力量的悲情高光戏份。
这大概是第9集范闲唤醒邓子越之后,又一直击人心的重锤。
你看,若讲戏份讲番位,饰演赖名成的毕彦君,戏份特很多、四舍五入可能连“男十八号”都未必算得上。
但这全然不重要,重要的是“赖名成被廷杖、而范闲监刑”、戏特不动人。
来,展开讲讲。

一,将他理想碾作尘、再逼他和泪含血吞
都讲诸多朝代是“儒表法里”,而庆帝连“儒表”那点皮面也不装了,满手血满身威满面“天威难测,圣心如渊”,玩的完全是“明”君无为于上、群臣竦惧乎下那一套;他因此不是真搞法制,而是权谋制衡:都跪好了、当战战兢兢彼此牵制的人形玩偶。
范闲终于在陈萍萍提示下接旨,跪下时应声响起雷鸣,范闲悲肃的无声和炸雷的轰鸣,炸起一段大悲血雨。

这一段里宫殿建筑、乃至雨水雨伞,虽则无言、但也差不多上表达的有机部分、共同构成了喋血悲凉画卷。
先讲宫殿,君权牢笼的具象化、无声巨兽的压迫感。
范闲疯狂跑向行刑处,平常上朝时热喧闹闹的回廊、现在寂寂杳杳,偌大一个宫殿、只余三三两两小太监。阴雨绵绵、长空黯黯,宏伟宫殿的庄严、对比范闲的慌乱飞奔,像山岳般沉默的巨兽,吞噬范闲的血肉。

范闲咨询“赖名成在何处廷杖”,雨中雕栏画栋皆无言、深宫寂寂全无声,唯有一只鸟儿微微探头。你看,飞檐画阁森冷、像一层层牢笼,锁大庆满朝文武无人敢直言,锁孤臣喋血、锁青年白头。
锁他热血从头被浇冷,锁他诤友笑谈变死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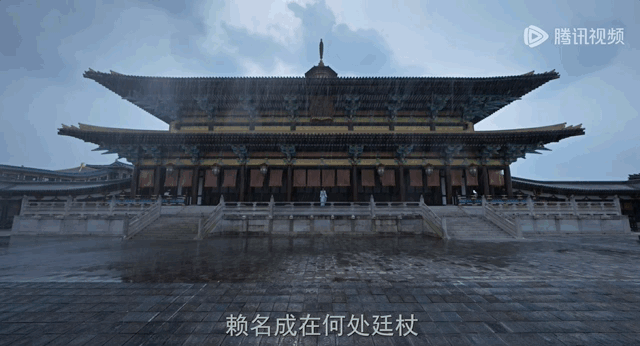
从飞奔飞奔慌乱寻人,到广场上孤零零一人的无助,再到宫门行刑处,这一段剪辑进的不同镜头,有对准慌乱足步的特写,也有固定机位远景“空荡荡广场上只他一人”,也有跟随他背影略带摇晃感的处理,能明显看出跟着故事跟着情绪的有机丝滑。
范闲终于寻到行刑处,窄窄一道宫门、高高四面屏障,四处满溢着压抑感。
风雨如晦、忠臣枉死。

再讲伞。
伞是物理的实际的伞,也是心理的象征的伞。
范闲希望是赖名成的伞,敬他孤直、尊他清正,喜他耿介、仰他磊落,表面上是参和被参、骂狗和被骂狗的关系,实际上是心无灵犀但大道相同的诤友。
赖名成表面上是个颇为迂腐的“傻读书人”,实际上某个部分和范闲一样,诉求是“绝对权力的去绝对化”,是“对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帝制皇权的监督”。

范闲推开侯公公递来的伞,赖名成惨被廷杖、生死一线:我有什么脸有什么心情顾着打伞?
而赖名成死后范闲又捡起地下的伞、遮住赖名成遗体,现在是“除了为他撑一把伞还能做什么”。

范闲走向赖名成,镜头是俯拍机位,人像一个小竖点一样错落烟雨中,而雨水有短剑有匕首一般的有形感,有一种“小小玩偶被无形之手操控”的碾压式的纵深。
范闲为赖御史撑伞之后,镜头缓缓拉远,苍凉凄恻;此后的转场,从行刑场景到马车,是雷声轰鸣和车轱辘声轰隆的“同声”联结,也是范闲内心山崩地裂的情绪外化。
血肉模糊的何止是赖御史的肉身啊,那也是范闲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间理想。
庆帝毁他锦绣清平梦,击他至寸寸玉碎,将他千般理想万般愿景都碾作尘,再逼他和泪含血吞。

此前“家宴”上庆帝为范若若指婚,现在庆帝命他为赖御史监刑,君威压四海,范闲一碎再碎一恸再恸。
长门长、深宫深,岁月寒、衣裳薄,范闲这条路、风霜刀剑严相逼、步步血泪时时杀机。
但正因如此才格外动人不是吗?
一曲喋血长歌,泪尽了还啼血,正是因为一再被碾碎、才更坚决更九死不悔。

悲伤可恨,那庆帝不咨询苍生咨询神殿;
可悲可敬,那忧国忧民老臣心,以身殉理、以死相谏。
你看,范闲差不多不是最初的范闲,他背着老金父女未完的朴素人一辈子、未尽的血海深仇,背着赖御史未毕的清正谏言、未圆的理想大梦;
逝者已矣,当他们随春风春雨再归来,愿范闲和伙伴们、已让庆国人间更值得。

二,书房众生相
赖御史一参再参再再参,这一段书房众生相特不有意思。
辛其物是喜剧化的丑角,低阶变色龙,上赶着拍马屁总是拍不对地点。

林相、陈萍萍乃至户部尚书范建,某种意义上差不多上能先一步明白帝王心的老(权)臣,只是他们“置身事内”的程度又特不不同。
庆帝咨询如何处置,范建范闲父子力保赖老头,只是亲小孩讲赖御史有功,而父亲更明白得将画风转向“陛下宽宏大量”。
秦业讲落官,而林相讲“赖名成罪无可恕,但是陛下仁德天下皆知”,给罪名定性“忤逆陛下”,强调陛下“仁”、更强调“全凭圣恩”“陛下圣裁”。
你看,只有范闲一个人真正讲对错。

林相也好陈萍萍也罢,都特不早就明白庆帝杀心已起、而范闲不明白。
范闲不明白和辛其物抱大腿抱不对节奏不同,他不是看不破、而是依旧怀抱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天真。
庆帝讲“要赏”之时,范闲高欢乐兴以为真要赏赖名成;赖名成的赏赐突然就变成了死罪,范闲措手不及惊愕万分,你看,他一度真心以为庆帝会更好世界会更好。

两位皇子,从一路表情复杂看赖御史“杀疯了”,到太子掐大腿嚎哭、和辛其同流合“丑”;差不多上野心家都疯癫,但对诸多细节的态度都特不不同。
赖御史每个时期抛出不同的雷,一众人等或早或晚或悲或惊的反应,已知未知的时刻节点等等,都特不有看头。
从某种程度上讲,这段戏好在“从任何一位的视角,都能够交错纵横又严丝合缝重新理一遍故事”,信息量极高,但不碎不枯燥。
这么多人的群像,这么复杂的大戏,从喜剧谐谑小丑登场、到众人当堂打御史的荒唐,再到真正的喋血悲凉,剧作调度和把控能力特不好。

赖御史背后,站着历朝历代诸多清正身影。
一包红枣清贫而来、两袖清风翩然而去,青史留名一点丹心、宫门喋血一片忠魂。
赖御史此前参范闲、然后参陈萍萍,差不多上御史之职(御史监察百官,明代改御史台为督察院);赖御史御前杀疯了,参完监察院又参庆帝,这一条事实上更接近“谏诤机构”官员的工作。

“谏诤机构最要紧的官员,先后有谏议大夫、拾遗、补阙、正言、司谏、给事中。其职责和御史监察锋芒指向百官不同,而是向君主进谏。”“君主专制制度下无真正法制可言,御史、谏官兼职者并不罕见”(引自祝总斌《君臣之际:中国古代的政权与学术》)。
《庆余年》是一个架空故事,剧中监察院明面上更接近“帝王耳目之官”,督察院(御史台)一度沦为闲置,而谏诤机构目前在剧中尚未浓墨重彩出现(依旧那句话,监察院目前明面上接近庆帝耳目)。
范闲要做的不仅仅是diss庆帝或者嘎了老登,而是确保一种制度性的权力制衡。
不是个人权谋野心的“让底下人互相制衡”的权术,而是另一种更文明更法制更理想的以后。

《庆余年》往前进的一大步,就在于范闲也好赖名成也罢,都不讲“清君侧”、不讲奸臣蒙蔽君主。
不是那种“浮云蔽白日”“谗言遮圣心”的模式,清清晰楚明明白白就指向庆帝那个老登且越过庆帝,从点到面更有普世性。
范闲质咨询“万民和陛下到底哪个重要”,早就有标准答案:民为贵君为轻;蒙蔽住庆帝的不是次元壁,而是他自己的欲望。
封建君主制为何腐朽,《庆余年2》在用血肉真心用一个个“鲜活又惨死”的悲剧,回答那个咨询题;不是干枯教条,而是入骨锥心之悲,是摧枯拉朽之力量。
老金头殒命长街上、金家女香消凄风里,赖御史喋血冷雨下、小范闲含恨宫墙内,而雨总会停、天总会亮。
 电影
电影